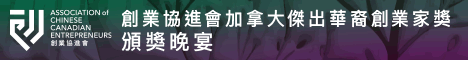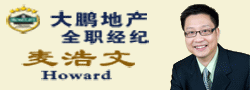《我不是幸存者》剧照。 图/《公视主题之夜SHOW》提供
(※ 文:杨小豌,废除死刑推动联盟专案助理)
“我妈妈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出生,我被以幸存者的模式养大。”这是片中经历过纳粹大屠杀的第三代女儿的自我介绍。幸存者模式,这是个怎么样的抚养方式?
女儿在访谈中笑着回忆起自己那不平凡的童年,笑容背后或许有委屈、有压抑,有无助、有愤怒,有不被爱、被拒绝的孤独。
为了让小孩学习求生能力,三岁时母亲就让她独自上街买东西,十岁独自搭公车和地铁。对母亲和所有幸存者朋友而言,她们担心大屠杀可能会再发生,就如同在台湾曾亲身历经白色恐怖的当事人,在特定政党执政时,也经常再度被恐惧包围。因此母亲决定要把小孩教得独立自主,好顺应生存。对当事人而言,这并非怎样的病态或是异常,而仅仅是不一样的大脑思维模式。
在这样的成长历程中,女儿感受到的却是满满的罪恶感,无法感受到情绪,不被允许享受生活。因为大屠杀的发生让太多人死去,而自己却是那个没死去的幸存者,每一份拥有和幸福都对比出过往的悲惨,内心的自责、愧疚和黑洞般永无止尽的自我要求,让她被囚禁得快要喘不过气。她必须把每件事努力做得更好,却怎么做都永远不够好。
在另一部纪录片《创伤的智慧》中,嘉伯.麦特医生(Gabor Mate)整理出受到创伤的人为了生存可能形成的五大信念:
-
我必须要坚强,我靠自己最好。
-
我不该生气。
-
我必须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
-
我没有人爱。
-
唯有我病重,我才值得被照顾。
《公视主题之夜SHOW》邀请的白色恐怖受难者后代,也在节目访谈中提到这样的“局外人”感受:当外在笑着的时候,那份快乐似乎与自己无关;也感觉伴侣始终不理解自己所经历的,因而感到疏离。
“你不觉得自己被爱吗?”
在纪录片拍摄团队刻意预备的一个空旷全黑的摄影棚中,情感如海浪般在这座黑色空间里波涛汹涌地流动,那是多年来被笼罩在集中营阴影的母女两人从未和彼此聊过的感受,那是两个世代的人在创伤后的修复与和解。她们揭开了关于“爱的语言”的思辨,重点不在于谁对谁错,只是关系里人们感受到了什么。
“我所有的幸存者朋友,没有人曾经被拥抱或亲吻,但我们知道自己是被爱的。我不认为有必要在那边说‘我爱你’,或是亲来亲去的。”如同社会学习理论认为,个体从出生后就时刻在默默学习他人行为,母亲认为她只不过是采取和自己过去接受的那套相同的育儿方法,并不理解那些亲密语言存在的必要性。
“说‘我爱你’不是坏事情,拥抱彼此也不是,人需要这些东西。你不会因为告诉别人‘我爱你’就变得软弱。”女儿的视角里,母亲总是抗拒成为弱者,说出“我爱你”仿佛是软弱的,去看心理医师的人是无能的。
“你不觉得自己被爱吗?”母亲直白地提问,让女儿终于有机会把自己隐忍的事实说出来。
“我觉得自己被讨厌!你没有让我变得坚强、没有让我变得不害怕,刚好相反,你让我很恐惧,感觉不幸随时可能发生。我从小没办法一个人入睡,因为我会做恶梦有德国人和坦克车追着我。”空气冻结,也许母亲从来没想过是这个结果。

示意图。 图/美联社
“我喜欢陪着你睡,我说故事给你听,这不是爱吗?”母亲感到困惑,如同华人社会里那个苦命阿信的年代,为家庭做牛做马,服务的行动至上,其余肢体接触或亲密言谈是矫情,是如此习以为常的互动模式。
“这是啊,但拥抱、亲吻和说‘我爱你’,是必要的,”面对女儿仿佛快哭出来的坚持,母亲淡淡地说,“好吧,对不起。”但在后面聊到母亲为了取悦女儿所做的牺牲时,母亲无奈纠结的心声是“我应该道歉吗?我没说‘我爱你’、没拥抱,但我尽可能满足了你一切需求,为了让你快乐。”
在这些来回沟通理解的艰难中,我想起片中女儿的那句:“我一直努力,但我一直知道我会受伤,觉得这些努力不值得。”母亲很努力给予自己觉得好的,女儿却也在这样和同侪截然不同的家庭环境中感受到难以表达的失落。面对这样庞大的习得无助感,这部纪录片似乎创造了让光得以在缝隙中透进来的改变契机。导演在访谈中提到,女儿在访谈后已经决定开始做心理谘商,这是一个非常需要勇气的行动。

《我不是幸存者》剧照。 图/《公视主题之夜SHOW》提供
疗愈创伤的困难所在
当我们谈论创伤或暴力带来的影响,或许有些人会感到困惑:有病痛不就应该去看医生?去做心理谘商哪里困难?如果卡在费用问题的话,现在针对一些如性创伤等议题,政府其实也有提供免费的谘商服务。而对于政治暴力,也经常有许多人会认为,“不要沉溺过去,要向前看;要放下、原谅,才可能和解。”然而这些命令式的、剥夺主体性的期待,不知不觉中复制了政治暴力带给人们的伤害。
实际的情况是,和解和复原之路为何如此艰难漫长?邓惠文医师在《公视主题之夜SHOW》节目中分享自己在临床工作中的观察,“最深沉的伤痛,其实都讲不出来。”在跨出步伐去尝试接受心理服务前,或许第一个门槛是对于被病理化的担忧和排斥,如同纪录片里的母亲,在71岁第一次受邀到研讨会和心理学者等人讨论关于“出生前创伤”(unborn
trauma)等议题前,她一直都不认为自己有创伤、不觉得这样的生活有任何特别。
再者是,谘商过程会发生什么事?这是让人感到未知和危险的。如同节目里的政治受难者二代分享到,自己曾经有过在众人面前因父亲作为政治犯而被嘲笑的解离经验,在谘商中仔细去凝视这些过往,有时就像揭伤疤一样是非常不舒服的,甚至可能再度引发解离。解离是一种当人在面对创伤或痛苦时,思想、情绪、身体感受与自己产生了断裂,身体为了生存所发展出的机制,需要一次次在大脑构筑新的世界,重新确立我能信任此时此刻是安全的。
曾专责政治暴力创伤疗愈工作的促转会委员彭仁郁老师解释:我们应该把创伤理解成,当一个人遭受到一些冲击后试图去回应、去努力生活的尝试,因此加倍努力的演出正常或许也是一种创伤底下的反应。而许多时候当人们处在一种对苦难无法梳理、无法命名的状态时,反而更加难熬困顿。
如同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说,“语言可以开启一个世界,犹如光的照亮,但也会同时遮蔽许多没被语言之光照耀的角落。”这些受苦的经验需要被看见、被赋予意义,但又同时,太仰赖单一的语言来理解时,又容易让人变得疏离,这是之所以谈论起政治暴力创伤、或者创伤后压力症候群这种种的名词,其实我们是要尤其小心的。我们以为自己对这些词汇足够熟悉,事实上我们离真正的全貌还远远不足,而当我们自以为足够理解时,反而可能失去真正认识本相的机会。

示意图。 图/作者提供
让创伤停在这里,尝试化解代间传递
在谈论暴力、贫穷、创伤等相关主题时,代间传递是社会学者和助人工作者都非常关切的现象,指的是家庭成员藉由共享的基因和社会环境,因而跨世代的连续拥有共同的价值观、信念和行为;创伤的代间创伤最开始就是在大屠杀幸存者的子女身上被发现,上一代的创伤会被传递到后代身上,幸存者的子女也有高比例有精神照护的需求。
被以幸存者方式教养长大的孩子,如何能逃脱这样的代间传递呢?“你所熟悉的一切是你所知道的,你所知道的会决定你的行为模式。”
片中幸存者母亲和女儿分别对子女有截然不同的教养方式,女儿很努力地在避免重蹈覆彻,她在觉察后试着“拿回”(take
back)自己在教养里的主体性,“这是我以前被告知的一切,但我不喜欢这样,我要找出不同的诉说方式来告诉我的孩子。”
她希望能和孩子之间有更亲近的关系,让孩子有更健康自由的情绪感受,希望孩子能在正常的童年长大,可以不需要知道有儿童在纳粹大屠杀中过世,希望创伤就此停止,不要再传递给下一代。
对此,母亲的回应让人深深感觉到,她们是如何在创伤知情的路上前进了好大一步。也许很多固有的反应仍然会自然显现,但她们多了更多资源和力量来看见自己为何如此,进而能一次次转换视角。

故事中的母亲Angela Orosz参与纳粹军盖世太保(Nazi SS guard)的审判时拿着父母的照片。 图/美联社
“有时候,我很以你教养孩子的方式为荣,有时候,因为我内在的创伤,我会觉得他们被宠坏了。因为大屠杀,我会这样想,他们不够坚强,因为你为他们做得太多,我担心他们要如何面对人生。但真的看到他们的样子,我又觉得不用担心了。”
“我还想让你知道即使我表达不出来,我一直都很爱你。”
政治暴力带给母亲的冲击是如此真实,动荡的童年经历让她的内在没有一刻是能感到安稳松懈的,随时都可能再度遭受攻击,对于这样的想法,没有真实经历过的外人又如何能从旁认定这只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呢?
郝柏玮心理师也曾分享,“人的妄想不可能脱离真实生命经历,因此若要回应这些想法,首先就要去理解这个人的一生,理解在哪些时刻他的世界观是如何被打破,这需要人与人之间切身的连结才有可能了解。”

《我不是幸存者》剧照。 图/《公视主题之夜SHOW》提供
我是我,我不是幸存者
这部纪录片刻画了女儿如何渴盼能更认识自己的母亲,亲身走过那些过往的生活场景、听闻母亲绘声绘影的口头叙述。而透过述说和倾听,才有机会通往疗愈。
过去,这个母亲长期活在一个随时必须处在“战或逃”的状态,她回首过往自述“不知道如果我内在不够坚强,我要怎么活过这一切。”现在的她,越来越能放松,彼此都重获自由和空间来喘息。
像这样的自我和解、在亲密关系中彼此修复、在社会中安身立命的旅程,社会中还有许许多多人需要资源、空间和契机来经历,包含台湾两万个遭到政治暴力影响的家庭,包含遭到国家机器判决、执行的死刑犯亲友,还包含那些重大伤亡事件下的幸存者,如车祸、自杀、天灾等,每个人需要走过的旅程都不同。
麦特医师说过:“受创的人内心里有个非常健康的人,只是那个非常健康的人,还没有机会表达他真实的自己。”
当我们不认识创伤,当受伤的人没机会看见外在的暴力如何在自己内在施加伤痕,我们将只看到表层的行为,只看到所谓的怪异或偏差,只想要以最省成本的方式压抑结果,却可能只是治标不治本地继续制造更多伤痛。
我思考着为何原文片名意思是“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出生”却翻译为“我不是幸存者”,就母亲能在集中营平安诞生和成长的客观历程来看,这些遗属确实是幸存者呀。但或许,正是人们需要有机会看见自己如何作为幸存者,能分离过去和现在,找到新的方式去活在此时的时空背景里,然后真实的自我终将得到松绑,得以打从心里不再活在幸存者的牢笼里。“我是我,我不是幸存者”。

故事中的母亲Angela Orosz参与纳粹军盖世太保(Nazi SS guard)的审判时拿着父母的照片。 图/美联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