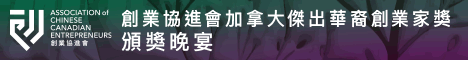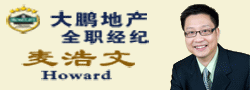【超级生活网 sUperLIFE.ca专讯】中国的文学评论界把2012年称作“薛忆沩年“,因为一年当中他一共有六本书出版,包括由上海三家出版社同时推出的长篇小说《遗弃》、短篇小说集《不肯离去的海豚》、随笔集《与马可.波罗同行》、《文学的祖国》和《一个年代的副本》以及在台湾出版的长篇小说《白求恩的孩子们》。 
薛忆沩在上海读书会上与读者交流
到了2013年年,他的势头仍然很旺,从年初到现在已经出版《流动的房间》(新版)、《出租车司机》(“深圳人”系列)和《首战告捷》(“战争”系列)等三部短篇小说集,并且有一部长篇小说在(《一个影子的告别》)在台湾杂志上连载。近年来,国内媒体称薛忆沩是中国文学界“最迷人的异类”,而这位受到文学界热议的小说家就住在加拿大的蒙特利尔,或者可以说是隐居在这里。接下来的两天,会播出梁彦对薛忆沩的访谈,了解一下:谁是薛忆沩?
梁彦(以下简称彦):虽然去年被称为中国文学界的“薛忆沩年“,但加拿大的中文读者对你并不了解,他们会问,谁是薛忆沩?介绍一下自己吧。
薛忆沩(以下简称忆沩):我六十年代中期出生于湖南郴州,四个月后迁回长沙,在那里完整地经历了“十年浩劫”。我最早受的是工科教育,本科毕业于北京航空学院计算机科学与工程系。后来我相继在湖南的研究所、大型国企、政府机关以及深圳的民营公司工作,每一段工作的时间都不太长。后来,我去广州求学。获得语言学博士学位之后,回到深圳在大学里任教六年。然后,我来到了加拿大,再一次回到校园,直到获得我的英美文学硕士学位。一位研究者称我的生活是不断的“逃离”。从上面的经历看的确是这样。但是,我从少年时代起就钟情于写作,并且矢志不渝。我是一个虔诚的写作者,对词语和句子的激情和深情没有随着年龄的增长,荷尔蒙的减少而出现丝毫的减退。
彦:在评论界写到关于你的作品的时候,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说,你的小说充满哲学的追问,尤其充满了对于个体生死的思考和分析。你从一开始写作就关注这些主题吗?
忆沩:是的。我的写作一开始就关注这些主题。24岁那年写出的《遗弃》就是很好的证明。这种倾向首先与个人的精神气质有关。我从小就对死亡极为敏感。在回忆“七十年代”的随笔《一个年代的副本》里,我标出了笼罩着自己成长过程的大部分死亡的阴影;其次,这与我们这一代人的特殊经历有关。在我们的求知欲最旺盛的时候,改革开放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存在主义”。我十六那年就订阅了《哲学译丛》等学术杂志。我至今保存着自己那时候读过的萨特的著名论文《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我在页面的空白处留下了大量的批注。对生与死的思考让“个人”,尤其是“个人”在历史中的命运成为我的写作的起点和重点。
彦:还有一个特点是“异乡写作”。2002年,你来到了加拿大的蒙特利尔。为什么选择蒙特利尔?异乡写作对你来说影响究竟在哪里?
忆沩:台湾的著名学者马森先生认为我选择蒙特利尔是因为白求恩,因为这是白求恩居住过八年的城市。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路。我相信我选择是一种与历史相关的选择,与精神生活相关的选择。我的写作从来没有受过功利的影响,异乡写作更是可以保持写作的纯净。还有就是语言,在远离陈词滥调的角落里,我突然发现了母语中那些从前被我忽略的美。这给了我信心和鼓励。这一点上来说,我是很幸运的。
梁彦(以下简称彦):你的作品中出现了白求恩,这个在中国家喻户晓的历史人物是你的名作《通往天堂的最后那一段路程》中“怀特大夫”的原型,后来更是长篇小说《白求恩的孩子们》的背景和基石,他是如何走进你的小说的?
薛忆沩(以下简称忆沩):他首先是走进了我的生命,或者说我们这一代在七十年代成长起来的人的生命。我们都是“白求恩的孩子们”中的一员,深受他“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的影响。而这种精神正好与今天在中国流行的价值观相冲突,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生活的悖论;另一方面,我在加拿大有机会读到丰富的白求恩档案,尤其是白求恩自己的文字,对他性格的矛盾有了深切的认识。于是,白求恩从我记忆中的单面的人变成了我想象中的多面的人。走在蒙特利尔的街道上,我经常会情不自禁地“进入角色”,用白求恩的方式与这座城市交流,或者用自己的方式与白求恩的阴魂交流。
彦:有意思的是,这两部作品在国内有完全不同的命运。
忆沩:是的。《通往天堂的最后那一段路程》发表非常顺利。发表之后,马上获得了极高的评价。在花城出版社2009年出版的“中篇小说金库”中,它与《阿Q正传》等十一种经典一起,作为金库的第一辑出版。今年五月,它的重写版在《作家》杂志 登出之后又一次激起热烈的关注,迅速被《小说月报》的选刊选载,并将被收入本年度的中国最佳中篇小说选本。而《白求恩的孩子们》获得的评价更高,认为它更加成熟。而且它的读者不仅包括中国最有影响的学者、编辑和出版家,还包括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蒙古的中国文学研究者和翻译家。但是,国内普通的读者却读不到它。三年过去了,这部作品仍然还只有台湾版,据说在香港的书店里,它被摆放在“大陆禁书”的书架上。但当然,它是非常文学的一本书。我是相信美学的,我相信一个作家的政治就在他的美学里面。
彦:还有一个关于你写作的话题常被提起,就是写作的艺术。评论家们会把你的作品结构与博尔赫斯、马尔克斯、或是卡尔维诺这样的一些作家相比。这些是对你影响最大的作家吗?你如何找到自己这种写作的感觉/方式?
忆沩:还有乔伊斯。我从小就受这些“作家的作家”对语言和结构的重视,对写作的那种“原教旨主义”的激情,这个深深地影响了我。加上从小就已经被白求恩的精神洗脑,我会将写作当成艺术,对它怀着“极端的热忱”,对它“精益求精”。这些都很根深蒂固。我可以为了一个词,一个标点思考很久。尤其到了现在,自己感到一个写作成熟的时候吧,对文字就更加的苛刻。
彦:在一篇访谈中,你说到,现在会重写以前的东西。你刚才也提到了你的作品的“重写版”。为什么要重写?这个过程是怎样的?听上去不可思议。
忆沩:是,我喜欢不可思议是个词。多种语言的冲撞导致了我对汉语的崭新感觉。在2007年前后重读自己的旧作(包括那些被评价很高的作品)时,这种感觉让我很容易就发现了作品中的许多破绽。我无法容忍那些破绽,于是从2010年开始重写自己的旧作。这个过程持续了整整三年。我的重写尊重原来的故事和情绪。我的重写带来的主要是语言的流畅和细节的丰满。它得到了阅读的肯定。
彦:有文章曾经评论说,刚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加拿大作家艾丽丝.门罗,文笔简练精准。但那是要经过几年的训练才练就的。你在文字技巧上的经验是怎样的?
忆沩:不是几年的训练,是几十年,是一辈子。如果说得简单一点,达到那样的境界当然需要的是“实践实践再实践”。但是,简练和精准其实是一个复杂又神奇的认知过程。它经常会让当事人和旁观者都有“成事在天”的感叹。
彦:你曾经说到自己每天的状态,从早写到晚,除了坚持长跑,还有每天晚上收听加拿大广播公司(CBC)的Radio 1。这样的写作状态真是太理想了。你怎么做到的?
忆沩:我能够一直生活在这种理想的状态中,靠的是对文学的狂热和虔诚,或者说对文学的“愚忠”。我曾经写过一篇题为《“好文学”的“坏运气”》的文章,回顾自己坑坑洼洼的创作道路,我当时是有点抱怨的。但其实实在是不必抱怨的。在文章的最后,我称写作者必须具备“红卫兵”的精神,你要对写作有一种狂热,一种虔诚,甚至愚忠,说的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彦:你的作品在中文文坛受到很多关注,你回国也越来越频繁。你会重新审视自己作品中的中国和现实的中国吗?总体感受如何?
忆沩:现在的中国被人们称为“比魔幻现实还要魔幻”,有些作家的作品会大量引用新闻现实事件。而我作品中的中国是我记忆中的中国,我的现实是历史中的现实。我只会写经过我的心智长时间咀嚼,并且已经彻底消化了的素材。回国的感受总是极为矛盾,一方面我看到自己的作品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和喜爱,这是一种享受;另一方面,发展已经完全摧毁了往日的痕迹,我们已经无根可寻了,故乡已经变成了面目全非的地方。这对我是一种折磨。
彦:评论界对你有一致的好评和期待。你自己对于被文学界,甚至国际文坛认可有什么样的预想?
忆沩:我的作品的确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权威和读者的认可。我从来没有关于认可的预想。在我看来,每一份认可都是奇迹。写作的魅力之一就是它不断让写作者与这种奇迹相遇。而我更看重自己的认可。这可能就是我用三年时间重写了自己大部分作品的原因。要知道,那其中有一些是得到了学者和读者高度评价的作品。你可以称这是“自恋”,也可以称这是“自虐”。我相信,作品本身是最重要的。写作者应该对努力写出“好文学”,而认可属于“好运气”,那不是他能够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