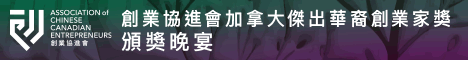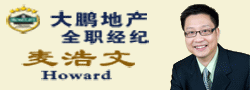诺贝尔文学奖新主爱丽丝·门罗是一位怎样的作家?羊城晚报记者独家专访门罗的文友、出版商、翻译者、研究者,多角度解读其人其事——
门罗宏观
瑞典文学院10日宣布,将2013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82岁的加拿大女作家艾丽丝·门罗。她是加拿大首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也是第13位获得这一奖项的女作家。
瑞典文学院常任秘书彼得·恩隆德当天中午在瑞典文学院会议厅先后用瑞典语和英语宣布了获奖者姓名,并将门罗称为“当代短篇小说大师”。彼得·恩隆德说:“一些人把她比作契诃夫,但她自成一派。她把这种特殊形式(短篇小说)带到完美境界。”他说,一些人称她是“北美最伟大的作家”,“我倾向于认同这种观点”。
瑞典文学院在当天发表的声明中说,门罗的作品以情节细腻见长,带有心理现实主义特色,有“加拿大契诃夫”的美誉。她的小说多以小镇为背景,描述主人公为了赢得社会承认而努力,却往往陷入紧张的关系与道德冲突之中。
身居加拿大的门罗在得知获奖后接受采访时说,自己在高兴之余“受宠若惊”。“我知道我在候选名单上,但我从没想到过会赢,”门罗对加拿大媒体说。门罗称自己一直把获得诺贝尔奖视为一个“可能发生,但很可能不会成真的白日梦”。她希望自己的获奖“能让人们把短篇小说视为一门重要的艺术,而非一个你写着玩的东西”。
1 曾是围着锅台的家庭主妇
爱丽丝·门罗本名爱丽丝·安·莱德劳(Alice Ann Laidlaw),1931年7月10日出生于安大略省休伦县温厄姆镇,父亲罗伯特·埃里克·莱德劳是养殖狐狸和貂的农民,母亲安妮·克拉克·莱德劳则是一名乡村教师。
她自幼喜爱写作,1950年,年仅十几岁、刚踏入大学校门的她就发表了第一篇短篇小说《方寸间的阴影》(The Dimensions of a Shadow),但当时并未引起什么轰动。
1950年,她考入西安大略大学攻读英语,但对于这门专业她似乎意兴阑珊,在短短两年内将许多时间用于打工,先后当过女招待、香烟销售员和图书管理员。
1951年,刚刚念到大二的她和同窗詹姆斯·门罗(James Munro)热恋,并很快与之结婚,并办理退学。此后,连生三女(其中一名夭折),1966年又生下第四女。
1963年,门罗全家从安大略省搬到太平洋沿岸的卑诗省,在该省省会维多利亚开设了一家名叫“门罗”的书店,这家书店生意兴隆,至今仍在营业。但爱丽丝·门罗在此期间却成为一名围着锅台和女儿们打转的纯粹家庭妇女,写作对她而言,似乎已成为遥远的梦想。
2 女权运动唤醒了创作梦
1968年是一个不平凡的年代,就在这一年,“五月风暴”从法国兴起,席卷整个西欧;同样在这一年,北美的反战运动和女权主义达到高潮。这一切似乎唤醒了爱丽丝·门罗尘封已久的创作梦,她开始挤出做家务、看孩子的空余时间从事创作,后来她女儿在2002年撰写回忆录时曾说,她之所以只写短篇、不写长篇,是因为在这段重返文学之路的艰难过程里,没有余裕创作大部头的作品。
这一年她出版了小说集《快乐影子舞》(Dance of the Happy Shades),一举荣获加拿大文学最高奖——总督文学奖,已37岁的她从此一举成名,此后两获总督奖(1978年《你算老几?》和1986年《爱的进展》),两获总督奖提名,两获吉勒文学奖(1998年《一个善良女人的爱》和2004年《逃离》),一获布克文学奖(2009年),此外还获得英、美、加多项文学奖项,这一系列奖项奠定了门罗在加拿大、北美乃至英联邦文坛的地位。
3 文场得意却感情失意
然而文场得意的她却经历了感情生活的波折:1973年她和詹姆斯·门罗离婚并重返安大略省生活,成为西安大略大学驻校作家,1976年她嫁给地理学家杰拉尔德·弗莱明,从此过着农场安居、静心写作的生活。
她的作品清一色短篇,且背景也几乎无一例外地放在最熟悉的安大略省休伦县,主人公几乎都是女性,且随着其年龄增长而由小变大,内容则通常涉及情感、工作和生活。她的笔触严谨简洁,充满含蓄美,名言警句不断,因此颇受出版商尤其是连载刊物的青睐,《纽约客》、《大西洋月刊》、《巴黎评论》、《女士》、《格兰街》等杂志都曾长期开设她的专栏。她的小说《大熊从山上下来》还曾在在2006年被拍成电影,差一点获得当年奥斯卡最佳改编剧本奖。
赞誉她的人称她是“当代契诃夫”,认为其小说人物心理描写细腻复杂,贴近生活和社会,但不以为然者,如文学批评家罗伯特·萨克尔则认为,她过于痴迷名言警句和个人风格,以至于忽略了情节本身的重要性,许多作品因此变得味同嚼蜡,甚至不近情理,仿佛只为支撑那些“闪光句”,甚至有人称“她写的只是段子,根本不是什么小说”。
一些人推崇她是“女权主义作家”,但也有人认为,她固然受女权运动推动重返写作之路,但本人并没有明显的女权主义思想。
4 短篇VS长篇的困惑
“现在,我们加拿大人有了一位属于自己的诺贝尔文学作者,她写温哥华的家庭主妇,写维多利亚的书商,写休伦县的农夫,还有我们身边的会计、老师、图书馆员——都是最普通的加拿大人,然后她用她的笔为这些人物注入魔法。”吉布森这位从1976年起就开始和门罗合作的加拿大著名出版商如此评论道。
当吉布森第一次碰到门罗的时候,她正陷入极度的焦虑和压力当中。1976年的时候,门罗已经出版了《快乐影子舞》、《我青年时期的朋友》、《少女们和妇人们的生活》,其中《快乐影子舞》还获加拿大总督文学奖。
但是,也正是在那个阶段,所有的人都在对门罗说,她不应该再继续写短篇小说,真正的小说家,应该写长篇才对。这时,吉布森给了门罗最强有力的支持。他对门罗说:“嗨,爱丽丝,他们错了。你就是个短篇小说家。你是短跑健将,不是马拉松选手。继续你擅长的。”而吉布森也不只是说说而已,他当时就向门罗保证会出版下一本她的短篇小说集,不管她写的是什么。也正是因为这样一群懂她的朋友在不断地为她加油打气,门罗将她的短篇小说继续写了下去,基本上每3至4年,就会出版一本小说集。
5 作风低调去年封笔
每个喜爱她的读者都知道,门罗是一位非常低调的作家,实际上她很少出现在公众视野中,也很少出现在签售会上,她只是不断地在写,写加拿大普通人的生活。她精确地记录女人们从少女到人妻与人母,再度过中年与老年的历程,尤擅贴近女性之性心理的波折与隐情,以及由此而来的身心重负,细致入微,又复杂难解,看似脆弱,却又坚忍顽强。
诺贝尔文学奖在门罗所获荣誉中,添下了重重的一笔,然而这或许也是门罗一生写作的总结了。现年82岁的门罗,已经决定封笔。在去年接受《环球邮报》采访时,她对记者说“我应该不会再写什么了。”老朋友兼出版商吉布森对此表示理解:“我很遗憾,但是爱丽丝已经82岁了,今年4月她失去了最亲爱的丈夫,她的健康状况并不十分乐观。不再写作——这是一个明智的决定。”
据悉,门罗曾于2009年进行冠状动脉手术及接受癌症治疗。她表示,获奖不会改变其封笔的决定。
6 创作灵感源于别人的故事
曾经有记者问门罗,她的创作灵感源于何处。门罗答道:“很简单,从别人的故事中获取灵感,有的是直接和他们聊天,有的是听别人间的聊天。”她说,语言是很奇妙的东西,经常很不经意地就走进了人们心中,而各种人的不同经历,也展现了生活的多元化。
对于写作过程,门罗指自己写得很慢,但基本都保持在一个稳定的节奏,无论是12岁还是81岁。“我喜欢早上起来喝点咖啡,然后才开始写。中途休息一下,吃点点心再继续,每次写3个小时左右。我也经常改写已经完成的部分,会为几个词而反复纠结很久,改了一遍又一遍,我想这也是为什么我只能写短篇。不过时间久了,我习惯并爱上这种在限制的空间里进行表达的方法,虽然有人喜欢更长一点的东西。”
门罗认为自己是一个“传统、幸运和自信的人”。“我喜欢说:Well, I can do it!”她说。
至于和父母、丈夫和其他亲人的关系,门罗说和大家一样,充满爱、恐惧和少许不满。而她最珍惜的东西是“记忆”。“很奇怪,当年纪越大,某些记忆就会变得越清晰生动,它们是你一路走来的见证,最真实的故事永远不会消退。” 编辑: 邬嘉宏
1
门罗翻译
“缺少门罗作品是个遗憾”
□羊城晚报记者 何晶
李文俊是首个中译本译者
著名翻译家李文俊是门罗作品首个中译本《逃离》的译者。得知门罗获得本届诺贝尔文学奖,李文俊在接受羊城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非常高兴,还说并不完全感到意外,“前段时间就有人告诉我门罗是热门人选”。
2009年,新经典文化出版了爱丽丝·门罗的小说《逃离》(Runaway)中译本,这部小说是门罗2004年的作品,全书由8个短篇小说组成,其中有3篇互有关联。
相比翻译福克纳的作品,李文俊说,门罗的东西好译多了,“她的故事比较完整,不怪异,作品里面的语言也都是普通人的语言,并不深奥,我需要把握的是怎么把语气传达出来”。
不过,李文俊先生也对记者表示,接下来他不会再翻译门罗的作品了,“因为我真的太老了”。或许跟门罗宣布封笔一样,他们都到了休养生息的年纪,李文俊生于1930年,比门罗大一岁,今年已83岁。
新经典方面表示,门罗的最新作品《亲爱的生活》(Dear Life)(2012年11月发行英文版)也将于近日与读者见面,译者是加拿大文学研究者姚媛。
门罗一直是出版社关注对象
译林出版社确认已签下爱丽丝·门罗七部重要作品的版权协议,分别是《太多的欢乐》(Too Much Happiness)、《快乐影子舞》(Dance of the Happy Shades)、《恨、友谊、追求、爱、婚姻》(Hateship,Friendship,Courtship,Loveship,Marriage)、《少女和女人的生活》(Lives of Girls and Women)、《公开的秘密》(Open Secrets Stories)、《一个善良女子的爱》(The Love of a Good Woman)、《爱的进程》(The Progress of Love),囊括了门罗早中晚各个时期最具代表性的短篇小说作品。出版社有关人士表示,作为国际一线作家和目前活跃着的最重要的短篇小说作家之一,门罗一直是译林出版社关注的对象,这一揽作品的引进版权早在今年上半年就已基本谈妥。
下月初《公开的秘密》将与读者见面,译者为秦俟全、邢楠、陈笑黎,其他尚未有中译本的作品,将安排最合适的译者开始翻译工作,预计明年陆续出版。
此外,羊城晚报记者还从九久读书人文化有限公司了解到,99短经典系列一直希望能出版门罗的作品,四年前就开始和有关方面商谈版权问题,可惜已被别家出版社早早拿下,“门罗一直是个热门作家,对于99短经典文丛而言,缺少了门罗的作品是个遗憾”,丛书策划者彭伦如是说。
八卦门罗
我对离婚后的她曾经“有想法”
□加拿大特约撰稿 黄运荣 陶短房
张翎(华裔作家):我和她分享同一责编
我的喜悦有好几重意义:首先她是加拿大作家;其次她是女性作家;再其次她是短篇小说作家。
加拿大文学在世界文学版图上还不是引人注目的一块,女性文学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也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短篇小说的体裁在很长时间里也没有像长篇小说那样引人关注。诺贝尔文学奖除了对门罗个人具有重大意义之外,它也将使得全世界更加关注加拿大文学、女性文学和短篇小说的创作。
当然,我还有更私人意义上的一层欢喜:爱丽丝·门罗的小说集《逃离》的中译本碰巧和我的几部小说都出自同一家出版社,我们有幸分享了同一位责编。几年前,我的责编才华横溢的朱丹女士就把这本小说集热情地推荐给我,我有幸认真地读完了它。
门罗笔下那些生活在安大略乡土上性格桀骜独特的女性,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对这位在短篇小说的土壤里辛勤耕耘了几十年并获得了无数世界奖项的作家来说,诺奖是一个完美的归宿。
陈红韵(华裔作家):她的作品被收进教科书
门罗获得今年诺贝尔文学奖,以她的文学造诣、成就和在加拿大的知名度,其实并不算是意外。也许华裔新移民对门罗不甚了解,但其实她的短篇作品,在加拿大很多学校都被收进英文课“Short story”部分的教科书,因此对于本地人来说,门罗和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 )一样,是青年人很早就接触熟悉的知名女作家。
叶兹Yates (教授、诗人):对她“有想法”经常请她吃饭
我曾和门罗一同参加过很多活动,对这个文学挚友的印象,可以用“温和安静,不太爱讲话,典型的加拿大人”来形容她,她看起来瘦小,不怎么和人讲话,但其实她都在观察着别人,在她的眼睛里,藏了很多东西,而心里更是孕育着丰富的想法,这也是为何她能创作出这么多令人喜爱的写实作品的原因。当年门罗和第一任丈夫离婚时候,自己还对她有过想法,经常请门罗吃饭呢。
琼·巴富特Joan Barfoot(作家):我居住在她成长的地区
我居住在门罗小时候成长的地区,她是那么完美,我很高兴。我读过她曾经写过和思考的每一个字,这是完美的。
崔维新Wayson Choy(华裔作家):确实是我们的契诃夫
你读她的一个故事,你认为你已经读一本小说……她确实是我们的契诃夫。
门罗微博
加拿大长期拿不到奖比中国冤多了
@彭伦空间(九久读书人编辑):爱丽丝·门罗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类似巴尔加斯·略萨获奖,对国际文坛来说,都是耳熟能详了几十年的名字。不过这是诺贝尔文学奖历史上首次颁给以为纯粹的短篇小说作家吧。某种程度上,也算是对短篇小说这一写作形式的追认和肯定。其实去年风传威廉·特雷弗可能获奖的时候已经初露端倪。
@洛之秋(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师):发给短篇小说作家确实是个意外,发给加拿大文学是实至名归。我在想如果韦尔蒂再熬几年不死是不是更可能得奖呢?阿特伍德这次错过了,很可能就再也没机会了,要论在英语文学中的文学地位,阿特伍德肯定是高出一大截的。当然,门罗成名已久,这次所有人(除了阿特伍德的死忠们)都会服气。阿特伍德就是太聪明了,绝精过了头,叙事显得过于花哨,这容易削弱感情的力量。
一直以来国内做加拿大文学研究的,都有些边缘化,究其原因就是缺了诺奖,难以正典化,似乎总隔了一层。加拿大文学的论文或项目都相对较少。其实战后加拿大文学真的非常出色,Margaret Laurence,Robertson Davies,Ondaatje,Atwood都是杰出的代表。这个国家长期拿不到诺奖,我觉得比中国冤多了。
@悦然(作家张悦然):总算有一年的开奖,完全没有读不懂的焦虑。门罗的大多数小说,情节性都很强。有时会过了头,给人用力过猛的感觉。比如《逃离》里的《播弄》,那是整本书里最不喜欢的一篇。而《逃离》里比较喜欢的篇目是《激情》和《法力》。太喜欢《激情》了,一小段什么也没有发生的激情。
@邱华栋(作家,《人民文学》副主编):还是徐则臣猜对了。今天在去遵义的路上,5点钟半途休息,我说今年是美国或者加拿大人得奖。如是加拿大就应是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排第一。但则臣说:不,82岁的爱丽丝·门罗得奖的可能更大,这样既可以表扬包括美国的北美英语文学,还给从未获得诺奖的加拿大一个礼物,又重视了短篇小说家,一举三得。 (何晶) 编辑: 邬嘉宏


门罗文本
偶然的窗口:从“桥上一吻”读懂门罗
□伊格言
偶然的窗口:
爱丽丝·门罗(Alice Munro)的作品主题往往过度细致幽微,而这样幽微的情感转折被包覆于极冷、极素朴的文字笔法之下,像土壤中的菌丝,像冰块中的气泡或针状杂质,不易为人发现,这直接导致了门罗的“难”。因此,能否读懂门罗,最主要的关键性因素即是能否对小说中的幽微主题有所感应。以下以《浮桥》为例(收录于短篇小说集《感情游戏》中)。
1
细微之处见结构功力
《浮桥》故事大致如此:尼尔(男)与金妮(女)是一对有点寻常又不太寻常的夫妻,其不寻常之处在于:其一,尼尔比金妮大16岁;其二,金妮得了癌症;第三,尼尔是个社会运动者。
长期以来,由于全心投入社运事业的缘故,作为一个丈夫的尼尔并不是个体贴的人。这点在小说中以几处细节表现——为了某些杂务,尼尔与金妮相偕拜访麦特与珠恩夫妇位于玉米田中的家。那是个朴实友善的农家,珠恩也盛情力邀尼尔与金妮两人入内作客。然而金妮才结束一段化疗,身体虚弱,不想进屋里去;因为一旦进屋,代表的是一连串寒暄问候等无法避免的应酬举措,对病人而言,那必然导致精神与身体的无谓耗损。于此,尼尔与金妮产生细微的意见不合:
“可是剩了好多豆子浓汤。”珠恩说:“你们一定得进来帮忙清掉那豆子浓汤。”金妮说:“谢谢。可是我什么都不想吃……”“那就改喝点东西。”……金妮向尼尔招手要他过她车窗来。“我没办法。”她说:“就跟他们讲说我没办法。”“你知道你会伤到他们的面子。”他低声说:“他们是好意。”“可是我没办法。不然你去好了。”他弯身更近:“你知道若你不去会怎样。看来会好像说你比他们尊贵许多。”“你去。”“你一到里面就好了。冷气真的会让你舒服些。”金妮摇头。
此处不提尼尔的身份(社运领袖)以及此一身份所带给金妮的长期不满——想当初,老娘我可是不顾众人反对嫁给你这个没行情的人;谁想到你满脑子只有你的社运,谁想到你对我并不体贴。事实上,作为一个组织者,尼尔必然有其世故之一面,对于人际间细微的阶级差异(以及因此差异而生的权力结构图像)必然有其适切的应对之道,面对所有可能发生的冲突、算计、妥协、权力分配与交际场——这是社运者的必要技能。
然而此刻,这样的“世故”带给金妮的却只有麻烦、只是困扰——老娘我才刚做完化疗,你就不能迁就点吗?
老娘金妮终究留在户外,没有进屋里去。她躲进玉米田去小解(更大的解放之前,一种小规模的预演,迷你版的“解放”——此处我们看见门罗的结构功力;先给出小的版本,再逐步推演至大的版本;先递出“试用包”,接着再奉上“一整瓶”),回来时便遇上了男主角瑞克。
2
短篇佳构独有的“神秘时刻”
少年郎瑞克是个餐馆服务生,麦特与珠恩的儿子——对,主题正是金妮与瑞克的姐弟恋,或者其实称不上“恋”:因为《浮桥》所开启的,不见得是爱情,不见得仅仅是爱情,而是笼罩于一切之上的另一种庞巨之物,一种可能性,一种阴影或光亮,生命中一扇稍纵即逝的窗口。是以门罗先是让这对初次见面的男女主角讨论了一件奇怪的事:
“是吗?”他说:“我也不戴表。我从没见过也不戴表的人。”她说:“对,从来不戴”“我也是。从来就不戴。……就像,我好像本来就知道时间。差个一两分钟上下。顶多五分钟……有时餐馆顾客问我,你知道几点吗,我就告诉他们。他们根本没注意到我没戴表。厨房有钟,我一有空就去查看。从没一次我得进去跟他们更正的。”
他们在讨论手表?当然不是。他们在讨论时间?不,也并非时间本身,而是一种“特异功能”,一种“对自然韵律的感知力”。X教授该来研究他们——他们体内自有其定时器,而此一定时器并不用以对应现实生活所规范的日常作息(手表),而是向自然敞开、向“人之本性”敞开、向“人”敞开。如此对话在初次见面时发生或许奇怪,却也十足合理:那原本便是一对陌生情人之间的调情,闲聊兼且试探——尽管难免别扭。
在瑞克体贴地询问金妮(“要不要我进去告诉他们你想回家?”“你累了吗?要不要回家?你要不要我进去跟你先生说你想回家?”“不要。不要那样。”“好。好。那我就不要。反正珠恩大概在里面给他们算命。她会看手相。”)之后,他们踏上了浮桥,那段命定的,未曾预期的旅途。而后终究遇上了那个令人印象深刻的“神秘时刻”——当然也是关键时刻——夜里浮桥上,男孩与老妇的深情一吻。
一个吻。一个神秘时刻。
事实上,不仅仅是门罗,绝大多数的短篇小说佳构必然建筑在每一个独属于它们自己的“神秘时刻”之上。小说的底牌就此掀开。
3
“桥上一吻”神秘时刻的到来
然而在此我必须先行引述另一细节——在走上浮桥之后,在深情一吻之前,一个镜头,一个安静的凝视:桥身轻微移动让她想象所有这些树和芦苇田都安在浅碟子上的土里,而路是条漂浮的土丝带,下面都是水。水仿佛这么静止,但又不可能是静止的,因为如果你拿眼盯住一颗星的水影,就看得出那星是怎么眨动变形又溜出视线。然后又回来了——但可能不是同一颗。直到这时她才发现没有了帽子。她下车小便时没戴,还有她和瑞克讲话时也没戴。麦特讲笑话时,她坐在车里头靠椅背眼睛闭上也没戴。她一定把帽子掉在玉米田里,而慌张中就把它留在那里了。
被遗落的帽子自有其象征,然而这不是重点。这顶帽子是个平凡的象征,其威力远不如在它之前关于水与群星的描述。浮桥之上,水恍若静止,但又不尽然——作者给了我们一个暧昧的“证据”——她形容,当你凝视着水面上的星星,那星星可能在极细小的波动中移动或隐没,而后复现──但可能不是同一颗。一种奇异的述写。像海面上的瓶中信,这镜头显然极其安静(在小说的氛围中、在那样数个空镜并列的剪接节奏里、在读者的脑海中),但其内容物又如此“有戏”,如此喧哗,如此充满张力。
那“不知是否是同一颗星星”的想法(一个带有哲思意味的微型议论)投影出一种虚幻感,而“水面摇荡中的星星”的实景同样予人虚幻之感。那不是星星本身,那只是星星暂存的倒影;那不仅仅是虚幻,那是双重的虚幻。在这虚幻的世界里,一切眼前实存之物(眼见之物)都仿佛只是蜃影。读者与小说主角老妇金妮在此结伴步上了浮桥,一趟奇异的旅途;而正是这神秘时刻的初现预示了下一个神秘时刻(桥上一吻)的到来。
我极喜爱此一细节。是这样的细节使得小说本身凌空腾飞于文字和情节之上——换言之,腾飞于它自身的有形肉体之上。
我记得小说家李佳颖曾做过一个极精彩的比喻:我盯着一个娃娃屋瞧,路过的人以为我探头探脑为的是那些可以放在手心里的小椅子、小电扇与小马桶。我试着告诉他们:不,让我着迷的是那个椅子与电扇之间形成的走道,洗手台底的凹处,马桶水箱下方靠墙的空间……但我用手指啊指的,说不出个所以然来。那些地方,那些罅隙,只有在东西摆对位置的时候才会出现;只有在灰姑娘一天的苦难结束,躲进去哭泣的时候,才会发亮;只有在不问灰姑娘家里怎么可能出现抽水马桶时,才会看见。
准确。小说家以其装置功力将人物、情节、意象等小说元素一一摆放于正确位置,为的正是那仅存在于虚幻之中的神秘瞬间——它偏偏就不是文字本身、不是人物本身、不是情节本身、不是意象本身;它是某种走道、凹陷、隐密的空间,它腾飞或隐藏于小说所构筑的现实之外——但也正是在小说家将人物、情节、意象、对话等实存之物全都摆对了位置时才能有效地将它由虚空之中召唤而出。在《感情游戏》中,门罗向我们展示的正是这样的基础技术。
4
整个世界变成了那个窗口
接下来故事进入结构上的高潮:一番试探之后,这对老少配在浮桥上接吻了。一个晃荡不安的吻(他们脚下并非坚实之地面,而是水面),黑暗的吻(因为太阳已隐没了,存留的仅有浮动不定的星光),秘密而怀抱着背德之刺激与快乐的吻(“反正珠恩大概在里面给他们算命。她会看手相。”),生命中一扇偶然敞开的窗口。对比女主角金妮的处境:她嫁给了比她大上许多岁却又不甚体贴的社运狂热分子,她是个病人,她刚做完化疗,拖着虚弱的病体──这是一场奇遇,一个神赐的礼物。
门罗的形容是这样的:“真可惜月亮还没出来。”瑞克说:“月亮出来时这里真是好。”“现在也好。”他手臂溜过来环住她,好似他这样做一点问题也没有,并且要多久就多久。他亲她的嘴。对她来说,她似乎生平第一次参与一个本身就是件大事的亲吻。
确实,这是个意外;然而在那一刻,那“本身就是一件大事”,或者,依我看来,那大事变成了“全部的事”──偶然的窗口扩大了,整个世界被窗口溢出边界的光所笼罩,世界变成了那个窗口。
偶然的事就是全部的事,像是一种自生命中逃逸的、歧出的另一种生命,仅为了此刻而存在;而原本的生命主体(一位社运者的妻子、一场意外疾病的袭击、一段有点幸福却又不会太幸福的婚姻)则逆反成为残余,成为赘物,成为幻影。那是人的深邃与神秘,生命本身如流体般变幻不定的可能性。仿佛天启。作者献给书中人的礼物(或者反过来说亦可:书中人献给作者的礼物)。
老太太门罗这样为它收尾:
回到干地后,金妮突然想到尼尔。
尼尔头晕眼花又将信将疑,手摊向那头发间杂亮丝的女人,摊向那算命师的凝视。在他的未来边缘摇摆。无所谓。
她感到的是一阵轻快的爱意,几乎像笑声。
一阵温柔的喜极之感,凌越了她所有的伤痛和空洞,在这短暂一刻。 编辑: 邬嘉宏
门罗研究
看阿特伍德像喝苦茶 看门罗什么感觉都有
□羊城晚报记者 何晶
短篇小说是加拿大强项
羊城晚报:单从文本出发,您认为门罗能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原因何在?
丁林棚:门罗的作品比较平实,很现实主义,但也有很多想象的成分,讲的是小镇中女人的故事,主人公大部分是女性。她的作品非常贴近生活,我觉得她的作品可能更能吸引女性读者。门罗获奖,我一点都不惊讶,她是加拿大最有代表性的作家。
羊城晚报:为什么是门罗而不是阿特伍德呢?
丁林棚:阿特伍德在加拿大的声誉非常高,从我了解的情况来看,包括加拿大国内评论界,认为具备实力拿下诺贝尔文学奖的,几乎都说是阿特伍德。但是,相对于门罗来说,阿特伍德可能缺乏心理的细腻描写。我一直研究阿特伍德,她的小说给人感觉她像是戴着机关枪的作者,全副武装,从情感的角度来说,她比门罗要欠缺不少。虽然我一直研究阿特伍德,但私下更喜欢门罗的作品。看阿特伍德的感觉,像喝了苦茶,而看门罗呢,是什么感觉都有的。
羊城晚报:能不能说,门罗比阿特伍德更能代表加拿大文学传统?
丁林棚:加拿大文学界自称,短篇小说是他们的强项,加拿大的短篇小说创作非常旺盛,优秀作品也很多。这可能和加拿大文学的起源有关。短篇小说短小精悍,能够在有限的篇幅内展现文学才艺,非常灵活。门罗是加拿大文学传统的代表。从早期到现在,都是写短篇小说,而且是系列的,读者可以分开看,也可以连在一块儿看。主人公或背景都是一样的,作者用不同的视角呈现生活中不同的时刻,门罗是这种文学传统的代表,她的获奖具有非常强的代表性。
我花了十多年时间研究阿特伍德,她和门罗的作品,我全部都有,从我的研究来说,门罗比阿特伍德更早获奖,我并不感到意外。门罗获奖,接下来阿特伍德基本没什么希望再得了。
加拿大文学研究
仅是学者的“副业”而已
羊城晚报:加拿大文学研究在国内学术界是不是比较边缘?
丁林棚:国内研究加拿大文学的,北京大学目前就我一个人,其他学校也有一些老师,但力量比较薄弱,位置比较边缘。我们的硕士博士论文答辩,很少有做加拿大文学研究的。每年都有加拿大文学学术研讨会,但大部分参会的学者是做“副业”的,完全做加拿大文学研究的很少。老一辈已经到了退休年纪,有两三个,比如南京师范大学的傅俊老师,年青一代比较好的,也就五六个人吧,比较少。
其实加拿大文学是非常有潜力,值得发掘的。加拿大国内有不少优秀的作者,很多外部读者不知道。在所谓后现代主义的当代,传统写作好像越来越少,但在加拿大文学创作中其实有很多,只是我们关注得少。
羊城晚报:西方学界研究加拿大文学的学者会相对多些吗?
丁林棚:在西方文学界,加拿大文学同样是边缘的。我曾在加拿大遇到一位当地的历史教授,他反问我说,加拿大有文学吗?想了想他终于说出一个作者名字,但这个人其实是美国诗人。甚至有人怀疑没有加拿大文学,国际学界也就只知道几个获奖作者。加拿大文学研究这块做得比较好的,有德国、英国、印度这几个国家,不过也是选取一两个有代表性的作家来研究,或者是与其有渊源关系的来研究,系统研究的比较少。
当然这跟加拿大文学发展有关。1860年代才开始有真正的加拿大文学,真正达到一定规模是在1920年到1940年之间,之前都是文学雏形,至少规模是不够的。1940年代以来,发生了很大的改观。
加拿大本国非常重视文学,到处宣传,资助文学研究,尤其是加拿大使馆,他们更希望拿一个诺贝尔文学奖来获得肯定,甚至比中国更迫切,毕竟中国文学历史悠久,有渊源,但加拿大文学最早也只能追溯到1860年代。
加拿大设有各种各样的文学奖,积极鼓励创作,推动文学的意识很强。不过真正懂门道的,不看总督文学奖,而是看吉勒奖,因为总督文学奖有政治代表性,每年的奖项一定有政治意义,比如今年给个小教派作者,明年给西部地区作者,后年给土著作者等等。而吉勒奖是完全从文学角度来评判的。
门罗获奖对加拿大文学有推动作用
羊城晚报:除了门罗和阿特伍德,还有哪些优秀的加拿大作者?
丁林棚:比如说玛格丽特?劳伦斯,她的短篇小说,初初读完觉得好像懂了,但会疑惑故事怎么这么平淡?但你仔细深究下去,里边有很多秘密,在很多小地方,你会发现故事完全不一样,那些你根本不在意的地方,可能就是整个故事最精彩的部分。她故意不写出来,留下空白,让读者来判断,是非常适合细读的文本,充满各种解读空间。
羊城晚报:有评论说,加拿大作者获诺奖是加拿大文学正典化的某种证明?
丁林棚:门罗的作品本身就是正典,原本受到的关注少,跟地缘、政治有关系。门罗非常低调,很少接触外界,她获奖对加拿大文学应该会有推动作用。 编辑: 邬嘉宏
门罗一直在坚守自己的创作
——大连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加拿大研究中心主任秦明利专访
□羊城晚报记者 何晶
羊城晚报:门罗以短篇小说见长,诺奖颁给短篇小说作者,这是历史上罕见的,您对她拿奖感到意外吗?
秦明利:并不意外。门罗的作品虽是短篇小说,但内容非常丰富,篇幅很多,涵盖了长篇的内容。但我也有点吃惊,因为另一位加拿大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呼声也很高。她俩相较而言,门罗比较潜心创作,阿特伍德近十年时间的社会活动比较多。从社会影响力来说,阿特伍德的影响比较大,她自己写作,也做广播、电视,利用各种媒体的优势。门罗只是坚守自己的创作,社会活动不多,批评性的东西也很少。
羊城晚报:您认为门罗的作品有何特点?
秦明利:她的文学性很强,是非常传统的短篇小说家。文学作品一般的传统主题,比如爱情、死亡、别离,等等,她写得比较多。因为门罗作品特别丰富,虽然每个短篇讲的是很简单的故事,但一个故事表达一个主题,作品多,涵盖的主题也就多。门罗的作品系列性很强,尤其是这么多年累积下来,整体来看,作品是有丰富影响力的。短篇小说其实是更容易打动人心,比如莫泊桑的《项链》,比如契诃夫的短篇小说,都很短小,但特别能够震撼人,艺术感染力非常强。门罗有很多短篇小说像寓言故事,读这样的短篇,读者会有种情感上的经历,从中有自己的感悟。门罗的创作数量多,但故事不重复,比如离别的问题,可以从多角度,以多个方式来讲。从语言上说,作为女性作家,门罗的语言比较细腻,但不是那种考究的,华丽的,而是非常平淡的,但平淡中玩味性很强,值得回味。
门罗出版
门罗作品国内版权全部签给了译林社
田智【译林出版社外国文学分社社长】:
我们一直关注爱丽丝·门罗的作品,但版权是今年才正式签下来的,之前她在国内的版权散落在几家出版社,有的买了但没有出版。我们跟代理商谈的时候,对方是希望国内能有一家出版社集中来出门罗的作品,集中打造一个作家,这正好符合译林社一贯的诉求,后来就把版权签给了我们社。
门罗是加拿大非常重要的当代作家,她一直专注于写女性,有人说她的文风神似契诃夫,她写生活、工作、爱情的失意,情节性不强,总是慢慢铺垫,最后给读者一种类似顿悟的感觉。正因为她的文字不华丽,国外有评论说她写作一个字也不浪费,每个句子都散发着光彩。比如改编成电影的短篇《熊从山那边来》,讲一对五十岁左右的夫妇,多年过去,有种失落感,门罗写他们遇到的困惑,最后让读者自己去体会和回味,这就是生活。
坦白说,就译林出版社的情况来说,曾经有段时间对出版短篇小说集比较犹豫,相对长篇小说来讲,短篇的风险会大些,这个感觉之前还是蛮明显的。但后来我们副总编袁楠出版了美国作家卡佛的短篇小说集,给了我们信心。当然,这不是最主要的,关键在于门罗确有文学价值。短篇小说其实不好写,鉴于篇幅限制,要表现得好并不容易。我认为,门罗的小说篇幅虽短,但内涵密度不输给一些大部头著作,这是她的力量所在,看似平淡的情节,但传达信息的密度非常强。
门罗擅长写女性生活,写的就是你身边的人和事,都是你熟识的东西,女性读者很容易就有共鸣,但文学总是相通的,作为男性读者,同样也能从门罗的小说中收获到自己的感触。(何晶)